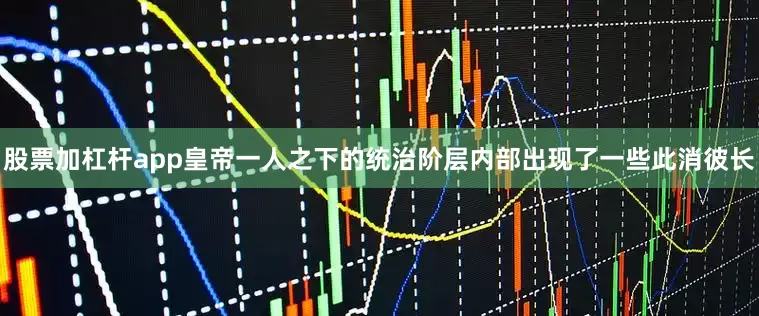

▲电影《长安的荔枝》剧照。(资料图)
全文共4416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他还在《长安的荔枝》后记中透露,写这篇小说的缘起,是在为写作《显微镜下的大明》收集素材时,注意到一份徽州文书里一个名叫周德文的基层小吏,他因负责物资调度劳累过度,病死他乡。
韩非曾将君王比作龙,将臣下向君主进言比作触碰“逆鳞”。故事里,上下臣工无一人敢向皇帝指出将岭南鲜荔枝运到长安的荒谬之处,是因为他们心知肚明,要君主做他不愿做的事,停止他不愿停的事,是触犯天威的危险行为。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
责任编辑|刘悠翔
“杨贵妃要是在马嵬坡没死真逃到了日本,是不是再也吃不到荔枝了?”2020年,一个朋友在微博上的无心之问让马伯庸脑洞大开,写出了《长安的荔枝》。从动笔到写完恰好11天,和小说中的倒霉小吏李善德将荔枝从岭南运送到长安的时间等同。
个体命运是马伯庸关切历史的落脚点,他在《显微镜下的大明》前言中表明了他的创作旨趣:“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往往会被史书忽略。”
他还在《长安的荔枝》后记中透露,写这篇小说的缘起,是在为写作《显微镜下的大明》收集素材时,注意到一份徽州文书里一个名叫周德文的基层小吏,他因负责物资调度劳累过度,病死他乡。《长安的荔枝》,就是从基层办事员的角度去审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故事。
2025年的夏天,《长安的荔枝》的电视剧版和电影版先后上映。电视剧版因“注水严重”被观众诟病,相较之下,由大鹏自导自演的电影版是一个更为成功的改编:电影的时长与阅读这篇9万字中篇小说的相当,叙事节奏明快多变。这部作品超越了逐渐泛滥的“窝囊受气中年男人”叙事,作了一番当下银幕罕见的直率表达。
1
荒谬的旨意

片中,李善德制作的运荔枝路线图。(资料图)
电影一开始,宦官鱼朝恩向上林署刘署令传达了一项皇帝的旨意:因贵妃诞辰将近,特设“荔枝使”前往岭南,运回新鲜荔枝。在唐代的长安,鲜荔枝只有做成荔枝煎才能保存。“荔枝鲜”与“荔枝煎”仅一字之差,但获取的难易程度天差地别。不善疏通关系的老实人李善德在哄骗下成了背锅侠,此时距离贵妃诞辰只有117日了。接下来的故事可以用电影宣传片里的一句话概括:“一颗荔枝的千里急送,一个小人物的命运狂飙。”
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离长安五千里。在那个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把荔枝送到长安,为什么没有人劝阻圣人呢?李善德在绝望中发问。他的朋友杜少陵(杜甫)虽然也官职不高,但比这个只擅长算学的小吏更清楚官场的门道,“圣人口含天宪,他定了什么,谁敢劝个‘不’字?”
“口含天宪”,意味着皇帝承载“天命”,代表“天”行使最高权力。西汉时期,儒生董仲舒革新后的儒家思想融入了帝制中国的统治原则,其中包括将皇帝神化。根据历史学家谢天佑的观点,自秦始皇开始,帝制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中都有一个独裁的皇帝,一切臣下都是听命于皇帝的仆役。
“君王既要利用臣子又不信任臣子,臣子既要依靠君王又畏惧君王,这种微妙的关系,就决定了君臣之间要玩弄权术了。”谢天佑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中指出,臣子需要用术来对付君王喜怒无常、复杂多变的心理,为官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学会把握向君王进言的分寸,避免杀身之祸。
韩非曾将君王比作龙,将臣下向君主进言比作触碰“逆鳞”。故事里,上下臣工无一人敢向皇帝指出将岭南鲜荔枝运到长安的荒谬之处,是因为他们心知肚明,要君主做他不愿做的事,停止他不愿停的事,是触犯天威的危险行为。于是就如谢天佑所说,“中国古代社会官场盛行讲假话,实则是畏惧专制独裁的心理状态的表现。”
在揣摩上意的同时,臣子之间亦要钩心斗角,躲避皇帝的猜忌,争取皇帝的宠信:岭南节度使何启光在得知李善德总结出了荔枝转运之法后,决定暗中阻挠送荔枝,因为如果从岭南向长安送荔枝那么容易,那之前那么多年岭南当局都不送,恐怕会给皇帝造成自己藐视朝廷、有谋逆之心的印象;杨国忠推动了李善德的荔枝转运行动,希望以此巩固杨氏一族的圣眷,鱼朝恩则担心杨国忠的得势将意味着自己的失势,下达了截杀荔枝使的命令。
唐代乃至整个帝制时期,最有名的善于纳谏者是唐太宗李世民。太宗朝,以魏征为首的大臣积极进谏,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君主的行为,成为一段佳话。魏征死时,李世民悲痛不已,亲自为之撰碑。但没过几年,他又疑心魏征生前有谋逆之嫌,下诏废止公主下嫁魏家,并且推倒了那面碑。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变化揭示了,专制主义制度决定了君主的忍让是有限度的,进谏的臣子头上始终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历朝历代,进谏和纳谏都是王朝政治生态的晴雨表。就这一点而言,观众不难意识到,荔枝使的任命书本身就是故事中玄宗朝政治危机的预兆——臣子对君主的监督彻底失灵,君主放纵私欲,为所欲为。
谢天佑认为,虽然从秦汉到明清,皇帝一人之下的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一些此消彼长,但整体而言,君主专制代表了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在剥削压迫农民阶级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之间利益是一致的”。历史作家谌旭彬在《秦制两千年》中进一步指出,绵延两千年的“秦制时代”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二是以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作为皇权与官僚集团的主要施政诉求。
《长安的荔枝》实则是从基层办事员的角度讲述了官僚集团如何为满足皇帝的一时兴起而榨取民脂民膏,“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李善德能算出荔枝转运的精确成本,但他算不出各级官员为逢迎上意,也为了一己私利,会层层加码地汲取人力物力。最终的结果是,为了成功抵达贵妃诞辰宴的那一瓮鲜荔枝,数十亩的荔枝树被尽数砍去,众多马匹和骑手折损累死,沿途驿站的驿户要多垫付六个月的驿站开销。附近的农户要么额外服徭役,要么缴纳两贯荔枝钱。那些本就贫苦的驿户不得不逃驿,附近的村民不得不隐姓埋名,远走他乡。

片中,为给贵妃送荔枝,荔枝农的果树被官府暴力砍伐。(资料图)
如果将视野转向历史无名者,会发现“大唐盛世”或许只是一种美好的历史想象。谌旭彬写道:“那是一个百姓纷纷脱离朝廷控制的时代。武周时代,宰相韦嗣立说的是‘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唐玄宗在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的诏书里也承认百姓‘逃亡未息’。”电影用一首说唱歌曲的篇幅快速呈现了李善德奔赴岭南的过程,心细的观众应该会注意到,主角与一队逃难饥民擦身而过。创作者将杜少陵安排为李善德的好友,颇具深意——正是诗圣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描述了属于平民百姓的,大唐盛世的另一面,并将之镌刻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
2
喜剧的忧伤

李善德为了拿到一纸政令在宫中四处奔走。(资料图)
电视剧和电影的创作者不约而同地以古装喜剧的思路改编《长安的荔枝》。大鹏本人演喜剧出身,自带喜感。除此之外,他还起用了众多喜剧演员和脱口秀演员,在电影的犄角旮旯埋下笑料。
不过这部电影的喜剧感,更多来源于“转换框架”(frame switching)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中提出,概念框架——经验的某种组织方式——构成了我们认知社会的基础,当我们转换框架,亦即将一件事去语境化并重新语境化,它将变得荒谬、震惊或滑稽可笑。
观众因从李善德的遭遇中看到“职场打工人”的影子和片中显得有些刻意的当代梗而发笑:年纪轻轻、不谙世事的李善德只身闯长安,立誓要为获得“长安户口”好好工作。有了妻女,在基层兢兢业业工作多年,他好不容易攒够本钱买了房,立刻又陷入每月还贷的烦恼。恰恰在李善德以为自家的小日子将越来越好的时候,天降横祸,他背上了“荔枝使”的黑锅,不得已踏上了一条翻山越岭、前途未卜的荔枝路。
李善德在偌大的皇宫里跑来跑去,被六部主事推诿踢皮球的情节令不少观众表示“共情上了”;杜少陵教给李善德的官场潜规则——“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也让人感到眼熟;荔枝转运之法则恰如那无情的算法,千年前和千年后的骑手皆被困于其中。
待故事情节推进至荔枝转运行动正式开始,喜剧色彩越来越淡,“官场现形记”的荒诞意味越来越浓厚:右相杨国忠赐予李善德一块象征“便宜行事”之权的腰牌,嗤笑称流程是强者不必遵循的规矩。原本对李善德不屑一顾的六部官员马上换了一副嘴脸,一群身着绯色官服的高阶官员向青衣小吏俯首听命。杨国忠空手套白狼地将转运荔枝的高昂成本转嫁到百姓头上,又借机为统治阶级敛财,苛捐杂税对平民百姓的摧毁性打击远比安史之乱更能让当代人感同身受。
立刻被动员起来的国家机器既是高效的,也是僵化难以变通的,当荔枝转运到了渡江的关键节点,只有原本希望攀上李善德的官府关系大赚一笔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富商苏谅尽释前嫌,驱船赶来,是因为朝廷的船都以“与公文所说的方向相反”为由拒绝前往。
电影解构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中几乎每一个关键元素。成百上千名骑手千里奔袭,只剩下李善德一人背着仅剩的一瓮荔枝抵达长安。夜色下,街边的屋舍内,有个青年与情人相会于花前月下,有个孩童背诵诗歌,被大人称赞必成大器。无人注意到大街上哒哒的马蹄,亦无人预见眼下的政治危机将在不久的将来以蚁穴溃堤之势摧毁长安。
自始至终,贵妃和皇帝的正脸都未出现,我们不知道贵妃是否因为那盘小心翼翼端上来的荔枝笑了,倒是李善德的妻子郑玉婷因见到丈夫平安归来露出了笑颜。电影更是用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镜头消解了这句诗隐含的“红颜祸水论”:贵妃捻起一枚荔枝的当口,鱼朝恩适时传唤安禄山献舞,吸引了贵妃的注意力。她收回了纤纤玉手,镜头从荔枝的特写拉远,那盘鲜红的荔枝从光彩夺目到泯然于各种奇珍异果之间。或许,荔枝从一开始就不是贵妃的主意,而是皇帝不负责任的异想天开,和统治阶级剥削百姓的合法借口。

片中的贵妃诞辰夜宴上,荔枝在满桌奇珍异果中并不显眼,甚至没有被品尝。(资料图)
电影难能可贵地没有回避权力倾轧的矛盾核心。大鹏的前作《年会不能停!》曾被部分观众认为董事长在年会现场突然主持正义的设定过于突兀。到了古装片《长安的荔枝》中,创作者有了更多空间去森严的权力等级制度中不堪的真相,把原著中李善德与杨国忠摊牌对峙的情节完整拍了出来。
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李善德感受过彻骨的绝望和权力的美妙,也见证了百姓在层层剥削下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唯唯诺诺了大半辈子,李善德在再次拜见杨国忠时忍不住质问:右相可知道,将一瓮新鲜的荔枝送到长安,在岭南要毁多少棵树,多少骑手奔波涉险,多少百姓流离失所,又有多少人为之丧命?
被杨国忠的金刚杵击倒在地,满脸是血,他仍在追问:锦绣长安,从何而来?
恼羞成怒的右相没有回答,但答案在银幕前的每一个观众心里。
(参考资料:《诗歌与警察: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秦制两千年》《显微镜下的大明》)
华亿配资-华亿配资官网-最新配资平台导航-炒股配资学习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